《中州启札》是元人吴弘道编纂的一部书信集,收录了金元之际北方一些著名文士官僚的202封信札。这些书信是研究大蒙古国及元初政治、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。这部书有两种刻本。它首先编成刊行于元成宗大德五年(1301)左右,是为元刊本。明成化三年(1467),翁世资重新刊刻此书,是为明成化刊本。目前这两种刻本均不易得见。清末陆心源(1838~1894)曾收藏一部元刊本,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。当代私人藏书家黄裳(1919~2012)曾收购一部明成化刻本。清修《四库全书》时,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两卷,但仅列入存目,辑本不知所踪。据统计,此书现有五种清抄本传世。现今学术界常见的清抄本有两种,一被国家图书馆收藏,北京图书馆(国家图书馆前身)1990年影印,收入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116册。一是南京图书馆收藏的清张金吾(1787~1829)爱日精庐钞本,齐鲁书社2001年影印,收入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》第79册。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清抄本都是据元刊本影抄而来,事实上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,它们分属不同的版本系统。对于这两个清抄本的源流,抄从何来,前人不明其详,甚至有所误解。本文拟考察这两个清抄本的版本情况,并辨别部分信札的收发归属,使学术界能够更好地利用这部史籍。
一 、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应是影抄日本静嘉堂藏元刊本
南京图书馆收藏一部《中州启札》,即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》据以影印的清抄本。《中国古籍善本目录》著录了这个抄本,书名编号“17805”,云:“清张氏爱日精庐抄本。佚名录清黄丕烈跋,清丁申校并跋。”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记其收有两部《中州启札》,其一为“明成化刊本”,另一为“影写元刊本”。抄本应即这部“影写元刊本”,前附丁申跋文亦称“是帙为古虞张月霄所藏影元抄本”。柳诒征(1880~1956)1948年编纂的《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》,称馆藏的《中州启札》:“元蒲阴吴弘道。抄本,丁书,善乙。”丁是指藏书家丁丙。丁氏《八千卷楼书目》载:“《中州启札》四卷,元吴宏道撰,爱日精庐影元本。”说明此书从张氏流入丁家,最后归于南京图书馆。
2001年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》影印收录此书,这本是一件嘉惠学林的盛举,然而却出现不得不辨的明显问题。在考察这个清抄本的源流之前,有必要先指出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影印本错误。影印本前有柳诒征(1880~1956)识、丁申(1829~1887)同治九年(1870)跋、许善胜大德五年(1301)序,后有黄丕烈(1763~1825)跋。学者介绍此书,也多提及这些识跋。柳诒征题识云:
此书馆中存两本。其一在续提善本中,惟后无《苇庵稿》。戊辰(引者按即1928年)十二月十二日,以两本对勘,此本序文第二叶第二行第二字“居”当作“君”。诗第四叶下第六行第一字“蟠”当作“幡”(续提本不误)。第五叶“僧对落花间”之“间”字,第六叶“宫粉凝成自洛阳”之“洛”字,均不误,续提本“间”误“开”,“洛”误“落”。并识于此。
《中州启札》是一部书信集,而不是诗文集,其中没有题识提及的文字、诗句,识文与这本书完全没有关系。南图藏的原本上截然无此识文。柳氏此识,实际上是为南图藏元人萧国宝撰《萧辉山存稿》而作。此书也收入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》第79册,题作《〈萧辉山存稿〉一卷附〈苇庵稿〉一卷》。识文提及的诸问题,与这本书的序及内容,完全相对应。影印者何以将柳识误植于《中州启札》清抄本前,不得而知。
又影印本开端,在丁跋、许序旁,可见钤盖有四、五方藏书印章,除两方可辨外,其余完全不可识别。而据南图藏原本,这些印章清晰可见,依次为“南京图书馆善本图书”“江苏省立图书馆藏书”、张金吾“秘册”“爱日精庐藏书”、丁申“强圉涒滩”等藏书印。“四库坿存”印章,本在丁申跋文上方,影印本误植于柳诒征题识旁。又原本在卷一首篇作者“赵闲闲”旁,有一丁家“钱唐丁氏藏书”鲜红印章(见附图2),影印本却了无痕迹。
再来讨论这个清抄本的源流。有关目录学著作及收藏、研究者,都称此抄本为影写元刊本。影写亦称影抄,严格来说,它不是随便抄写,而是用薄纸蒙在原本上,按原书字体、行款,照样描着抄下来,连框栏、甚至是前人藏书印记都描摹出来。2014年制定的《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?第一部分:古籍》对影抄本的定义是:“依据某一底本覆纸影摹其图文及版式而成的古籍传本,又称影写本”。按照这个标准,此本则不能称之影抄本。现知该书唯一一部存世的元刊本,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。《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?解题篇》,其中详细记录了元刊本的版本信息:
版式:左右双边(一九?八×一二?二糎),有界,每半叶一三行,每行二二字,注文双行二二字。版心黑口,双黑鱼尾。
抄本虽描有版心,但无鱼尾、边框。将抄本与静嘉堂藏元刊本细相对照,可以看出,虽然行款、文字抄录全遵元刊本,但两本字体并不一致。元刊本是当时刻本习见的颜体字,抄本则带有典型的赵体风格。抄本中几处抄写讹误,也说明并非原样蒙描抄写。
实际上,出于对古籍善本的保护和爱惜,很多抄写者采用对临,而非覆纸影摹的方法传抄古籍。宽泛的定义,也称这类对临摹写,在字体字形上不同的抄本为影抄本。按此说法,此本称为影抄本也无不当。前人曾经使用“影录”一词,大约是注意到了对临与覆纸抄写的不同,试图加以区别。依此意见,则此本应称为影录本。
一般还认为,这个清抄本曾经张金吾、丁申校补。依据是张金吾、丁申等人的志、跋。张氏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明成化刊本《中州启札》条云:
元吴宏道编。影元抄本中多阙文兼有误字,藉此得以校补,亦快事也。
许善胜序。
翁世资重刊序(成化三年)。
志文提到的“影元抄本”,应即他所藏的“影写元刊本”。抄本前附丁申跋文有云:
是帙为古虞张月霄所藏影元抄本。……爱日精庐尚藏成化间翁世资重刊本,得以校补元抄阙文。
《中国古籍善本目录》称抄本“清丁申校并跋”,当是据此而来。然而这一认识并不准确。丁申跋文续云:
《藏书记》录许氏序文,兹先以朱字补写其阙。倘异日成化本得复插架,俾成双璧,必更意蕊舒放矣。书此以待。
《藏书记》当指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,其“影写元刊本”志文,全文抄录了许善胜为《中州启札》写的序。丁氏不直接依据明成化本收录的许序,而选择《藏书志》抄录文字“补写其阙”,已是可疑。跋文期待成化本“得复插架”,显示其并未能利用到明成化刊本。丁跋作于同治九年(1870),张金吾已亡故四十余年,其藏书渐已散出。丁氏虽得此抄本,但恐怕不易得见明成化本。所谓“爱日精庐尚藏……,得以校补元抄阙文”,更可能是依据陆氏《藏书志》,转述而来。
丁申所谓的校补工作,其实只是补写了序文的缺字而已,这从其云“兹先以朱字补写其阙”即可概知。按图索骥,抄本中仅见许序中有若干朱字,“言”“相与切”“也朋友尺牍”“以至亲戚音”“昏丧祭等事”“士大夫从事”“纤以为工”七处(参见附图1)。笼统言丁申校补了此抄本,显然并不准确,容易让人误解丁氏校补了全书。
张金吾称藉明成化本“得以校补”影元抄本,但恐怕并非是说自己校补了该书。事实上,校补该书的另有其人。在抄本若干页面的天头处,间有小字提示,如卷一第四、五页中,“此下元刻似脱一页”。又卷一第六、七、八页顺序颠倒,实际上当分别为第八、六、七页,这几页中间有两处小字,一提示第七页“此页似接第五页”,一提示第八页“此页似接第六页,由装订时因口沿残破,以之不为次耳”。有研究者误解这些小字提示“应为柳诒征所识”。在卷一末尾留白处,也有小字标注,云:
嘉庆己卯(1819)六月二十四日,校于新市舟中。梦华。
梦华是清代著名藏书家何元锡(1766~1829)的表字。除此之外,还有卷二第十二、十三页中间小字:“此三十四字当作小注,元板已如此。”卷二末尾“连市舟中校”,卷三末尾“含山道中毕此卷”,卷四末页“原校‘询问’疑当作‘絇间’”“二十四日未刻,舟次乌镇,校毕”。这些小注字迹一致,都应该是何元锡在1819年六月左右校勘时写下的文字。
何氏与张金吾交好,同是藏书家,经常互通有无,这年七月还一同访书。张氏曾购其抄本,托其抄、校书。这个清抄本原属何氏所藏,后归张氏,还是张氏托其抄写、校补,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可以明确,何氏细致地校补过该书。何氏云“元板”“元刻”,他依据的当是元刊本。陆氏所谓依明成化本校补,意思恐实指可藉此校补抄本。实际上似乎并未利用明本校补,这从抄本仍有较多缺损可知。这些缺损基本上也是元刊本缺佚的部分,明刊本不至雷同如是。
这个清抄本据以影抄的,其实就是现藏于静嘉堂的元刊本。首先,元刊本前补抄的序及卷一前四页,被抄本原封不同的照录照抄下来。《静嘉堂秘籍志》称元刊本:“序及首四叶抄补。”元刊本在许序后留白处书有“吴草”二字,当是吴姓抄补人所书。第四页第十行末尾有小字“接下文去”。表明了这几页系抄补而来。抄本卷一前四页,行款各异,看起来不像是元刊足本的原貌。元刊本的行款是每半页十三行,每行二十二字。此抄本卷一第一、四页半页十三行,第二、三页半页十二行。每行字数,即使是同一页,从二十一到二十六字不等。第四页下半页仅十行文字,留下为承接下页文字而权变的明显痕迹。抄本这四页显然并非据元刊足本而来。对照静嘉堂元刊本前补的序及卷一前四页,抄本与之文字、行款完全相同。
这个元刊本抄补的许善胜序,有七处空白缺字,清楚可见。抄本前附丁申跋云“兹先以朱字补写其阙”,随后的许序用红笔补缺有“言”“相与切”“也朋友尺牍”“以至亲戚音”“昏丧祭等事”“士大夫从事”“纤以为工”七处。恰与元刊本的缺字空白处严丝合缝。卷一首页《与杨焕然先生》中“未能照管馆”,“管”为衍字。“人之士人”,“人之士人”,前一“人”实为“今”误。第二页《与中书耶律》,“浑源刘祁及其弟李仝”,“李仝”前漏一“郁”字。同页《与白枢判兄》“报鍭山已娶妇”,误“铁”为“鍭”。细检抄本,则是完全承袭了这些错讹衍误。抄本的这些特征,昭示它就是据这个残缺经过补抄,而非别的元刊本抄写而来。
其次,对照元刊本元刻页面的残损、缺字,可见二者渊源。除了抄补的前几页外,元刊本保存下来的元刻页面,因时间久远,水渍虫蚀,出现了纸张破损、文字漫漶、残缺的现象。卷一最为严重,其余各卷稍好。细细查对抄本的缺字页面,如卷一第五页,上半页第二行下“人”之后缺两字,第十一行下“奔诣太原留百许日”,“许”字只留下言字旁,“日”字缺。第十二行“今奉去”以下缺多字。下半页首行第二字缺,下“录寄”后缺二字,第四行“宁复”后缺一字。卷二第三页上半页后三行,分别在“道雅意”“与老妻”“至愿足”后脱两字、一字、两字。卷三第三页下半页头两行,“不肖观凡”“谨作书引诚”后小块脱漏文字,第五页上半页末两行,“常以”“慰慰仆”后缺多字。检之以元刊本,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其脱漏缺损之处。限于篇幅,仅举数例。事实上,将两本的缺字部分细相对照,即可知此本实据此元刊本而来。
通过对照之后,还可知道,在此抄本抄写之后,历经岁月,元刊本还新添若干细微的损失。如卷一第十页,除两本都有的文字缺损外,上半页第十行“国家”二字,下半页第六行“起居介”三字。第十一页上半页第十一行“专价”的“价”字,第十二行的“兹引”二字,下半页首行“然之意其”,第二行“闻”字。这些文字抄本俱有,元刊本已缺不可见。此外若干文字出现磨损模糊的现象。这当是原已破损的地方,渐及周围所致。古籍收藏保护之难,可见一斑。
有证据表明,何元锡校勘时,利用的也是这个元刊本。前文已经提及,何氏在卷四末页天头处,小字注云:“原校‘询问’疑当作‘絇间’。”在元刊本的相同位置,也有批注文字,虽模糊几不可辨,但依稀可见:“‘询问’二字,疑当作‘絇间’。”后似还有文字,已漫漶不可识。何氏所谓的“原校”,当即指这个元刊本上的批注文字。这个元刊本应还经过修补。卷一第五页上半页左下,有明显的拼贴痕迹。第六页上半页《与吕子谦参议》的篇名之下,虽缺损,仍有“百”“丞旨”三字可识,下又有“而使”二字。抄本上不见有此数字。这几字当是后来修补粘帖上去的。修补者错行拼帖“而使”二字,致使它们居于作者署名“王百一(丞)[承]旨”的下面。
这个版本最接近元刊本原貌,而为其他几种清抄本所不及。台湾“中央图书馆”藏两种清抄本,一为刘氏嘉业堂旧藏,行款半叶十三行,每行二十二字,无格。据缪荃孙《嘉业堂藏书志》云:“此本系劳巽卿从影元抄本影录。”另一为张蓉镜(1802)旧藏,半叶十二行,行二十二字,显然与元刊本行款不同。日本静嘉堂文库还收有陆心源原藏的一种抄本,陆氏《皕宋楼藏书志》著录其为“旧抄本”。这三种清抄本,以及下文讨论的国图藏清抄本,或行款不同,或间接来于元刊本。相较而言,现存这几种清抄本,唯有南图藏本最为接近元刊本,在静嘉堂藏元刊本不易得见、明刻本秘不示人的情况下,这个清抄本具备较高的版本价值。它忠实原书,文字秀美,抄写精善,应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。此本还保留了元刊本的错误,这应该是何元锡有意为之。何氏校勘抄本,并不改动元刊本的讹误,忠实依据原本,做到“不校校之”,实可宝贵。
需要指出的是,此本抄写出错,留下些许瑕疵。如许序“辍己俸锓梓”,抄本误“辍”为“辄”。卷一第十一页,“相公”误为“相父”。卷二第五页《与李才卿寇子益杨元甫》,“火来刑金”,误“火”为“大”。第六页,篇名《与孙谦甫》,抄本误“甫”为“府”。卷三第十四页,文字“高斋号颐贞”,误“贞”为“真”。卷四第九页,“前日贵司所假甲样”,误“贵”为“实”。又卷一第七页,“德甫子清二书”,“甫”字抄漏,于正文旁以小字补。这些都是对临抄写常见的错误。元刊本则均不误。笔者目力所及,仅见这几处小误。
附带讨论一下现存元刊本。日本静嘉堂藏元刊本,系出陆心源皕宋楼。检元刊本,上有“马玉堂”“笏斋”“吴江凌氏藏书”“凌淦字丽生一字砺生”“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”“归安陆树声所见金石书画记”等藏书印。是陆氏所藏之前,历经马玉堂(约1815~1880)、凌淦(1832~1895)等人。而在此之前,应是藏于黄丕烈。黄氏曾有题跋云:
郡城故家李鉴明古遗书,残麟片甲,约有百余种,其可取者三四十册而已。至宋、元旧刻,无可为披沙之拣,唯此《中州启札》,尚属元刻。检钱少詹《元史艺文志》总集类云:“吴宏道《中州启牍》四卷。”与此正合。虽钞补而仍缺失,取其稀有,故存之,不复分与讱庵矣。李氏书,与余友张讱庵合得。乙亥二月十四日复翁。
乙亥,1815年。张讱庵,即与黄丕烈同时的藏书家、苏州人张绍仁(字学安,号讱庵,一号巽翁、巽夫)。据文意,黄氏得“元刻”《中州启札》于故家、明代藏书家李鉴(字明古)的遗书之中。此跋明确是为元刻本所题。缪荃孙也记黄氏曾收有一部元刊本。黄丕烈所撰藏书题跋经后人搜集编纂,有多种作品传世。是跋系于“《中州启札》旧钞本”目下,当属误置。黄氏确有一部旧抄本,后亦归陆心源,现也藏于静嘉堂。今藏静嘉堂元刊本,后有黄氏跋文。经比照,可确定旧抄本“所存之黄跋当是过录者,非亲笔也”。《中国古籍善本目录》不知南图藏抄本忠实抄录元刊本,包括序、跋,称“佚名录清黄丕烈跋”,以为黄跋是后人补缀。跋文中“虽钞补而仍缺失”,抄补应是针对元刊本前附的序及卷一首四页等处所言,依黄氏所言,这些抄补当完成于明代李鉴收藏之际。
在元刊本的许序前,有一个两页纸的跋文,首段云:
杨太后,南宋宁宗后也。才敏好学,作宫词五十首,久已失传。洪武中,钱塘贡士家有钞本,为之刻梓。
其后附写五首宫词。这些内容与《中州启札》全无关系。当是页数单薄,收藏者一并装订保存。或是如南图藏清抄本的影印者一样,误植于此。
在这个元刊本的天头处,除上文提及的末页外,还有多处间有批注文字。大多漫漶,或因裁边而字画残损。这些批注,有校正文字的,如卷一第四页第五行,“遇”字由“乃”字改夺而来,天头处写一“遇”字以正之。或提纲契领归纳信札内容的,如卷二第二页上半页《与耶律惟重》,天头处写:“答耶律生问真西山、朱文公二公诗说不同。”卷三第五页王显之《与吕子谦》,天头处写:“吊慰。”或解释信札中字句的,卷三第十二页下半页《与王经略》,天头处有一段较长文字,解释信中“款段”“下泽”词义,有“款段马”“下泽车”“援传注”等字,因裁剪页边,而致部分截去,不能通读。这些文字不知为何人所书,年代必在何元锡1819年校勘抄本之前,或为黄丕烈,或为李鉴,于今至少已有两百多年。
二 、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的源流与价值
国家图书馆也收藏一部《中州启札》清抄本,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1990年据以影印。此本前后无序跋,无法明确它的版本源流和收藏流转。《中国古籍善本目录》书名编号“17806”,只记录它是“清抄本”。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》略详,注录:“清抄本,一册。十三行,二十二字,无格。”抄本首页钤盖四方藏书印,分别为“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”“延古堂李氏珍藏”“古香楼”“休宁汪季青家藏书籍”(见附图3)。由此可知,此抄本曾先后被清初汪文柏(1659~?)、清末民初李士铭(1849~1925)两位藏书家收藏。1930年代,李氏后人李宝训将大部分藏书售予北平图书馆,《中州启札》当是由此归藏国图。
此本行款与元刊本一致,格式统一,抄写工整,很容易让人以为它是影抄元本而来。但细相比较,此本只是采用了元刊本的行款格式,并非影抄。页面文字、行款与元刊本完全相同的仅有13页,不到全书四分之一。造成页面不同的原因,主要有两个。一是此抄本漏抄个别字,但仍保持每行二十二字,致使不同。如卷二第四页,此本漏抄“见”“以”,致使这一页有四行与元刊页不同。二是元刊本节约纸张,一行挤占超出二十二字,或占用信头篇名空白处,而此本不然。如卷二第十一页一信札末字“也”,此本独占一行。元刊本则挤占于一行,致此行二十三字,同时致此页多抄出一行,以及以下几页的第一行、最行一行不同。卷三第一页下半页第四行“宣”字,卷四第七页上半页第第十行“悉”字,元刊本都是占用了下一封信的篇名空白处。
此抄本字迹秀美,堪称精善,但也有多达十六页存在文字缺损现象。只是比元刊本的缺字情况要好,多数只缺数字而已。因此可利用二本相互对勘,补正文字。如卷一第六页,元刊本有大面积缺文,此本略有缺字。但缺损区域不同,彼无此有,相互对照,两本都可补全。元刊本由于页面残损而遗漏的署名“冯内翰”“王百一(丞)[承]旨”,可依此本补全。此本卷四无名氏撰《与张宣抚子敬》“谨依命分礼海都……”,“分礼”不可解,依元刊本,当作“分付”为是。
此本还有经过校勘的痕迹,在多处正文中间用黑笔傍注小字,校改或补漏原文。如改“制文”为“斯文”,“四十人”之上添“三”字,“某顿”与“再”间插入“首”字。校勘似乎不止一次。除用黑笔傍注、圈改外,还有用朱笔点窜校改的情况。如点“洛”“待”“特”为“洺”“行”“持”,改“小”“再”“勤”为“心”“某”“劝”,旁添“子”字。元刊本不存在这些误、漏,这当是抄手不谨所致。对比元刊本,这个清抄本还脱漏了较多的信札作者署名,如郝陵川、王淡游、宰鲁伯、勾龙英孺、胡德珪、王器之、王仲谟等人。这些脱漏或缘于它抄录的原本漫漶、残损。
此本在文字上与元刊本有一些不同处。有些可以补正元刊本的讹误,如卷一元好问《与中书耶律》“浑源刘祁及其弟郁、李仝”,《与白枢判兄》“坐是不得奉起居之问”“铁山”,卷四晋汝贤《与游宣抚子明》“以病中不能相饯”,元刊本漏“郁”字,误“坐”“铁”“病”为“生”“鍭”“胜”。又元刊本卷四无名氏《与王侍郎子勉》“自顾行李萧然,不能为无计奈何,谨遣韩掾……”,“不能为无计奈何”,殊不可解,此本作“不能为计,无奈何谨遣韩掾……”,语意通顺。
还有一些文字与元刊本相较,有着明显的不同。如卷四王构《与张可与》“有弟不归去,自愧耽之深”,“自愧”,元刊本作“世味”,无名氏《与游宣抚》,“计惟莅政以来,钧侯起居清胜”,“以来”,元刊本作“权舆”。从文意上看,二者皆通。这些诗文没有其他史籍可用来作对勘,孰是孰非,尚难确定。这种显著不同,不像是抄手擅自径改,当有所本。与南图藏清抄本类似,此本也存在页次错误的现象。卷四第十二、十三页顺序颠倒,不知是其本身装订错误,还是所据原本有误,抄本沿袭而来。
这个清抄本的价值不容低估。此本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,它是现存几种抄本中最早的一种。书上藏书家汪文柏的印章,说明此本最晚成书于清初。根据上文讨论此本与元刊本的一些不同,颇疑此本来源于明成化刻本。张金吾曾称“影元抄本中多阙文兼有误字,藉此(按指明成化本)得以校补”,黄裳亦称明成化本“实较元板为善,以误书反少也”。此本正符合这些特征。惜乎明成化本今不可得见。此本若是抄自明刻本,为何全作元刊本行款?又明本前有许序,后有重刻人翁世资跋,此本全无,难道如黄裳所言,“估人撤去”,冒充元刊本牟利?这些疑问暂时没有答案,只能悬空待明。
附带谈一下明刊本。此本未见国内外有藏,唯黄裳称曾于1950年购到一部。黄氏1952年的跋文,著录了明刊本的版本信息,云:
《中州启札》四卷,成化刻。十二行,二十四字。大黑口,四周双栏。前有大德辛丑四月朔承事郎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许善胜序。后有成化三年莆田后学翁世资跋。
不幸的是,黄氏藏书后来在文革中被尽数抄没,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才陆续发还。不过这本《中州启札》似乎佚失,不在发还之列。黄氏1979年为《中州启札》又写一跋,与上跋互有详略,可相互参照。此跋收入1985年出版的《翠墨集》中,但却列于“云烟过眼新录”目下,表明此书已不在黄氏手中。此书现在何处,是否尚存世间,已然成谜。
三 、部分书札的收发归属
上文已述,这两种清抄本可相互比对,校正文字。除了两本对校之外,还可利用其他数据对这部书信集进行校勘。如元好问、许衡、刘因等人有文集传世,又元人编《国朝文类》、《天下同文集》,明刘昌辑《中州名贤文表》,清张金吾编《金文最》,也都收有部分作者的书信。尽管如此,由于大部分作者没有文集留传,或者文集中未收这些信札,可以利用的资料,仍是非常有限。关于《中州启札》这部书的文本校勘,除花兴辨正一组有关彰德路的信件外,还未见有较深入的讨论。本文拟对花文作一些补充,同时考察若干信札的收发归属问题。
花兴在文中指出,十封署名杨果、王恽的信札有误,作者应该是高鸣。署名杨果的有九封,分别为《与姚左丞雪斋》《与史丞相》《与藏春国师》《与赵平章宝臣》《与张平章仲一》(四首)《与王左三部侍郎子勉》。署名王恽的一封,《与杨正卿参政》(二)。花文利用信中提及遭遇旱灾、请求减免治下赋税,以及待罪相下和遣知事马某等信息,结合杨果、王恽、高鸣等人的任官履历,判断这些信札当撰于中统二年(1261)左右,归属时任彰德路总管的高鸣,而非杨、王。花文的判断是正确的,但可作两点补充。
一是还可确定两封书信应当归属高鸣。卷一署名徐威卿太常(按即徐世隆)的《与张平章仲一》,云:
某呈某阁下:时夏,伏惟钧履曼福,调鼎优游,神明孚佑。敝邑不幸,自去岁九月至今不雨,二麦尽损,秋稼不能立苗,百姓忧虞,无法可救。今差发已降,输纳之力寔不能任。谨遣知事马某从纳怜曲中前往告请,万望相公以平生利物之心,力为分解,方便奏请,量加轻减,甚大惠也。惟相公鉴裁。比遂参谒,切冀为补赞大器自厚。不究。
其中提到“时夏”、旱灾、“遣知事马某”、请求“轻减”差发。这与上述十封信札的内容完全一致。这封信也应当归属高鸣,而不是徐世隆。
“纳怜曲中”一名,还曾出现于《与藏春国师》信中。花文对此人未作考察。此人实属蒙古宴只吉台部,自1257年始,到至元六年(1269)死去,一直担任彰德路达鲁花赤。事迹具见胡祗遹为他撰写的《大元故怀远大将军彰德路达噜噶齐扬珠台公神道碑铭》。由于传世胡氏《紫山集》只有四库本,其中人、地等蒙古语译名多被馆臣篡改。有研究者已经辨明“扬珠台”即“宴只吉台”,而对“纳琳居准”原名不明所以。据这封信札,可知它的元代译名实为“纳怜曲中”。由纳怜曲中的身份,也可证明这一组书信,确属高鸣无疑。身为彰德路知事的马某,随从上司达鲁花赤纳怜曲中,前往告请灾免,实是情理中事。
另一封是卷四佚名撰《与刘尚书才卿》,云:
某顿首再拜上某阁下:拜违风度,不胜倾向。迩来未审雅候若何。某不肖,治郡无效,想刑政区处之间,多所谬误,故天降沴,为百姓忧,罪谪之大,无可言者。今遣某人专往哀请,实望相公从容救疗,倘于贡赋之中获赐蠲减,非惟一路疾苦遽然慰释,虽某不肖,亦知古人果有二天之说矣。希赐孚照,未趋侍间,切冀善自珍啬。前膺大拜,以副天下士大夫之望。不既。
刘尚书才卿,即刘肃,《元史》有传。中统元年,任真定宣抚使,二年,授左三部尚书,寻兼商议中书省事。王恽《中堂事记》载中统二年六月四日,“真定宣抚刘肃授吏户礼三部尚书”。信中“前膺大拜”,或即指此。信当撰于中统二年六月以后。写信人又“治郡”,遇到天灾,遣人“专往哀请”,希望“蠲减”贡赋。这与上面讨论高鸣的情况很相符合。再联系到高鸣在中统二年左右为彰德路灾情事,遍写书信给朝廷要员,如中书省宰执史天泽、赵璧、张易、姚枢、杨果,左三部侍郎王博文、忽必烈倚信的“藏春国师”僧子聪(按即刘秉忠)等人,他同时写给负责经济事务、任左三部尚书的刘肃,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这封失题作者的信札,也应该归属高鸣。
二是这十二封信札的撰写时间,可以确定在中统四年夏。花文依据高鸣、杨果的任职时间,推断写作于中统二年之后,无疑是对的,但还不够精确。由这些信札中反复出现“盛暑”“炎暑”“暑溽”“时暑”“时夏”,“久旱”“旱”“灾”,及“郑司直”“马某”等信息,可知它们应当撰于同一时间内。其中一封“呈左丞相公先生阁下”的《与姚左丞雪斋》,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信当写于中统四年(1263)正月后。姚雪斋即姚枢,《元史?世祖纪》载:“(中统四年正月)丙戌,以姚枢为中书左丞。”又《与藏春国师》信头曰“具呈国师上人”,说明此时僧子聪(刘秉忠为僧时的法名)尚未还俗。子聪还俗,改名刘秉忠,《元史?世祖纪》记在至元元年(1264)八月。信札应撰于至元元年八月之前。又《元史?世祖纪》载:
(中统四年八月壬子)彰德路及洺、磁二州旱,免彰德今岁田租之半,洺、磁十之六。
这条资料中有关减免彰德路田租的信息,当是对高鸣这一组请求信札的回应。这十二封信札,应该撰写于中统四年夏。其时史天泽、赵璧、张易、姚枢、杨果、刘肃、王博文都在中央机构中担任要职。经过高鸣的努力,这年八月,元廷决定减免彰德路田赋。
还需要指出的是,归属高鸣信札中的五封《与张平章仲一》,这个篇名并不恰当。中统元年,张易任为中书参知政事,二年,升右丞。他任平章,是在至元七年。五封信称之“某阁下”“相公”,并不见平章官衔。标之以《与张平章仲一》,当如钱大昕所言,是“纪前事而称后官,文家往往有之”。
除了以上提及的,还有一些信札的收写归属问题值得探讨。首先是卷三署名王恽的《与杨正卿参政》(一),云:
某顿首:霜寒,敬惟别后起居多福。昔在燕,极荷眷顾,仆今秋大葬于钧,近复还京。今岁久旱,晚田不收,麦种未下者三之二,物价未复向日之贱矣。可虑可虑。李国瑞处见右丞相书,始知已到燕京矣。令嗣大哥想只在左右。侯唐杰行,谨此奉闻。未卜良会,千万以时自重。不宣。
卷一署名杨果的《与姚都运》(三)云:
某顿首公茂阁下:霜寒,敬惟起居康吉。仆去岁三月出燕,行李忽忽,相别吾相于鞍马上,不能款曲下马一拜,迄今为慊。仆今岁以葬事,在钧者数月,近复还京,衰老之迹,殊不足为吾相道。友人侯唐杰行,姑此上闻。良晤未期,更冀惠时自重。不宣。
两相对照,可知这两封信应出自同一人之手,不当分别属于王恽、杨果。由第二封写给姚枢的信中称自己“衰老”之语,写信人应该不是王恽。其中称姚枢为“吾相”,当写于中统四年姚任中书左丞之后。又按杨果曾长期居于河南,中统二年,任中书省参知政事。至元六年正月,出为怀孟路总管,时年七十三岁。这与信中提到的“衰老”,“昔在燕”“去岁三月出燕”,“大葬于钧(钧州,今河南禹州、新郑一带)”“以葬事在钧者数月”等信息相吻合,这两封信的写信人当是杨果,撰于至元七年冬。那么,第一封信的收信人就不应该是杨果自己。其中云“李国瑞处见右丞相书,始知已到燕京矣”,这封信很可能是写给曾任中书右丞相的史天泽。
第二封信由信头“公茂阁下”,可以确知是写给姚枢,但篇名标以《与姚都运》,不大恰当。按据姚枢行实,未见其曾任都运一职。有关姚枢的碑、传,只载他于宪宗蒙哥即位后,曾向忽必烈建言,“请置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图宋;置都运司于卫,转粟于河”。《元史?世祖纪一》载:
(岁壬子(1252))太宗朝立军储所于新卫,以收山东、河北丁粮,后惟计直取银帛,军行则以资之。帝请于宪宗,设官筑五仓于河上,始令民入粟。
当即设置都运司一事。姚枢很可能于此时短暂任过都运一职。至元七年,姚枢已拜相、任中书左丞多年,杨果写给他的信札,篇名当然不应是《致姚都运》。这很可能是多封写给姚枢的信放在一起,笼统起的篇名。
其次是卷一署名冯内翰(1162~1240)的《与刘太保》,应当不属冯璧信札。信云:
某顿首再拜仲晦国师上人:昔尝奉阁下屡荷提诲,感感佩佩。今欲拜见王府,业已行矣。以久不见阁下,渴心摇摇,庶此行敢陈卑恳,不意事侫中止。信哉行止非人所能也,谨遗行人,以代面酬,即欲言者,谨具别幅。静中希一电瞩,更望回赐片言,一砭膏肓,幸甚。身滞心驰,不胜倾祷之至。时秋尚暑,千万以军国自重。不宣。
按冯璧长刘秉忠(1216~1274)五十余岁,当不至于如此谦卑,写信用“屡荷提诲”“渴心摇摇”“敢陈卑恳”这样的语句。又刘秉忠1242年方随僧海云北上,初见忽必烈,进入王府,开始成为蒙元前期政治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。1240年去世的冯璧,不可能给1242年后的“国师上人”僧子聪写这封信。写信人决非冯璧。太保是刘秉忠至元元年八月还俗之后才有的官位,信头尚称他“国师上人”,篇名显然也不恰当。
其三,卷二许衡《与廉宣抚》七封信札,收信人不尽是廉希宪。其中最明显的,莫过于第七封信,信头云“郎中心契执事”,可知这是许衡写给一位任职郎中的官僚。按廉希宪履历中,并没做过郎中一职。许衡文集《鲁斋遗书》收录此信,题《与人四首》,没有明说收信人身份。明刘昌编《中州名贤文表》亦有收录,题《与某郎中》。收信人都没有作廉希宪。《中州启札》应是误列廉氏名下。
第四、五封信也比较明显。两信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,即希望得到收信人帮助,辞去京兆提学一职。信中有云:
畏辞纳于宣抚廉公,未承见允。忧惧熏心,感疾如旧,不能起者旬日矣。其不安之势可心意晓。
累复求于宣抚廉公,冀为回奏,未见允许。忧惧熏心,至于卧病,其不安之,先生可想见也。
两信都把“宣抚廉公”当作叙事的第三者,称辞职请求未能得到廉的允许。收信人不可能是廉希宪。《鲁斋遗书》同样没有告知收信人,只收入《与人四首》中。又按两信中言辞切切:
陈辞于左右,冀复款于仲晦、仲一洎诸君子。……以谕抚司,得申卑恳,不胜拜赐。
恃爱旧,愿致此意于仲晦、仲一二君子。
请托收信人向上文提及的“国师上人”僧子聪和元仲一(张易法名)这两位当时深受忽必列信赖的王府僚属致意,转达辞职的意愿。联系到张文谦与刘秉忠、张易,以及他与许衡之间的密切关系,《中州名贤文表》收录这两封信,篇名《与张仲谦左丞》,应该是正确的。第六封信《鲁斋遗书》收入《与人四首》。其中有语“未知先生以为如何”,称呼、语气与上两封写给张文谦的信相近,刘昌列入《与张仲谦左丞》,似有一定的道理。
《中州名贤文表》还将第三封信也列入《与张仲谦左丞》,第一封信篇名作《与赵宣抚相公》。《鲁斋遗书》则仍视第一、三封的收信人是廉希宪,收入《与廉宣抚三首》。这两封信中透露的信息有限,不足以判断孰是孰非,只能存疑。
四 、余论
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将馆藏的《中州启札》清抄本予以影印出版,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对此书的使用和研究。藏于日本和台湾的元刊本、清抄本,虽不便查阅,也可得见,唯明刊本难觅真容。丁申曾感慨说“倘异日成化本得复插架,俾成双璧,必更意蕊舒放矣”,如果有一天这几种版本都得以影印利用,对于研究者来说,将是一件幸事。
除了两三篇文章提及,或者用到这部史籍中的信札作相关探讨外,目前学界对《中州启札》的研究还不多,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。事实上,信札中包含的丰富内容,不仅有助于考察当时士人间的关系网络与讯息沟通,还有助于研治金元之际、元初的政治史等诸多层面。归属高鸣的几封书信,真实地反映了中统四年左右彰德路地区的灾害情况,可以与《元史》记载相印证。此外,还可补充正史记载的不足。元初名臣张易,《元史》无传。唐长孺先生曾着《补元史张易传》,囿于史料缺乏,于张易中统二年十月到至元三年正月间行实,仅推断他在至元元年左右由行省平阳、太原“旋召归”,于三年任同知制国用使司事。由高鸣写的几封信札,可以判断中统四年夏前张易已返回中书省,故而高才写信求援。又结合许衡写给“仲晦仲一”的几封书信,可知张易实是中统元年前后,忽必烈幕府、元廷中地位超出他人的显赫人物。又王博文,《元史》亦无传,相关史料亦极疏略。由高鸣信札,可知他在中统四年左右,任职左三部侍郎。《元史》有传的刘肃,本传及《元朝名臣事略》载他中统三年致仕,仍商议中书省事,“四年卒,年七十六”。由上文揭示归属高鸣的《与刘尚书才卿》,可知刘肃当卒于中统四年夏之后。有关姚枢的碑、传资料,都失载他曾任都运一职,据《与姚都运》信札,可补足这一行实。
囿于篇幅,本文仅作以上阐发。《中州启札》中还包含较多的信札收发归属、文字辨正与信息解读诸多问题,这些都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。
附图:

1、南图藏清抄本书影一

2、南图藏清抄本书影二

3、国图藏清抄本书影一

4、国图藏清抄本书影二

5、静嘉堂藏元刊本书影
(附记:本文资料搜集、核查,获得访日学者、暨南大学助理教授乔志勇博士,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研究馆员郑小悠博士,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展可鑫博士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郑旭东博士,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、南京图书馆国学馆,暨南大学陈广恩教授、博士生邵婵同学等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。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魏崇武教授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宝海副教授,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陈仁仁教授,历史系李洪财副教授、助理教授向珊博士,沈阳师范大学讲师魏曙光博士、美国南加州大学刘海威博士,均曾给予有益教示。一并致以谢忱!)
本文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副教授,文章原刊于《清华元史》第七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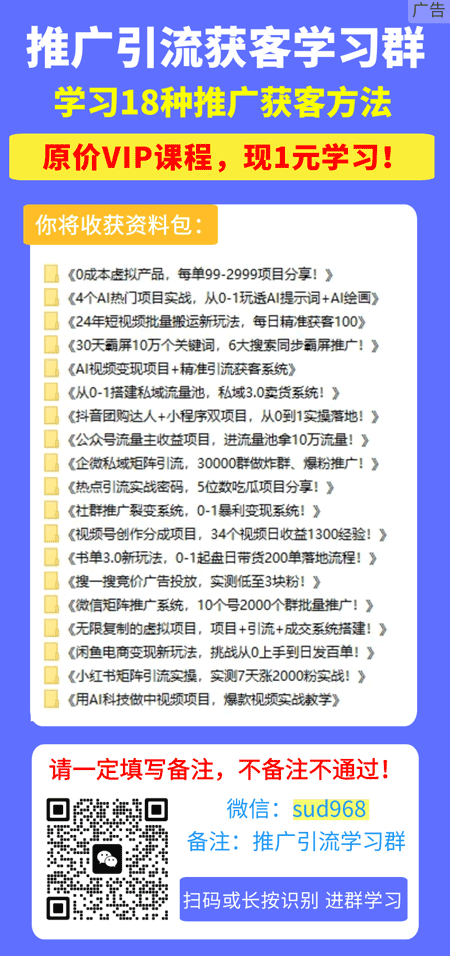
原创文章,作者:admin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seohomer.com/8862.html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