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夜过去,一天又到终末。
那高悬于九天之上的金乌鸟渐渐西沉,投在鹰落塔顶上最后一抹赤红的光辉开始消退。
风信子扶着梯子蹲在青砖瓦墙上,抻着胳膊,伸了个懒腰。
今夜轮到他跟几位叔伯兄弟巡逻了,那几位都是庄稼汉,个顶个的魁梧。他若混在其中如哈士奇进了狼群,又像是小鸡仔一样看着就脆弱不堪。
“苏家兄弟!苏家兄弟!”
正在神游的风信子听到有人在叫,声音是下面传上来的。
他低头一瞧,是猎户,果然是在跟他说话。
“是猎户大哥啊,找小弟有何吩咐?”
“夜里凉,吴阿伯叫人炖了骨头汤,去喝一碗吧。这晚上在外奔走可不比屋子里头,虽说离冬天还远,可也不好受的。”
猎户摇摇头说道。
风信子这才发觉到,猎户竟披着一张毛皮,看上去品相不太好,东缺一块西缺一块的。尽管如此,风信子瞧着也是暖和的。
这便是老江湖和小菜鸟的差距了吧。
风信子想着,忽地就理解了那一句:‘少年不识愁滋味,爱上层楼。爱上层楼。为赋新词强说愁。’
他生在这个庄子里,从小在田里林间嬉戏打闹,却好像从来没有真的低下头观察过平民老百姓的生活。明明自己也只是个小民而已,哪里来的毛病呢?什么时候有的毛病呢?
可若说没挣过银钱,却也谈不上。
他能写文,也写得一手好字,县里也算是排得上名号的。乡绅大小家族有什么正式的会面交际都喜欢请他去帮忙写几个字,润笔费什么的自然也从没短缺过,比起在黄土地里深耕的老农来说,清闲无比,得的钱财也更多。
他凭什么不能自视甚高呢?
可今日却忽地明白了,他风信子,他苏家小子,从来没真的懂过这庄子上的人。
“苏家兄弟?你这是怎地了?可是病了?”
猎户抬头看墙上那人,只见他又不说话了,不知是什么意思。
风信子回过神,没说什么,顺着梯子爬下来。对猎户说道:“猎户大哥先去,我随后就到。”
“行,那我可就真不管你了。”
“我这么大的人了,还能让自己饿着不成?猎户大哥身子壮,对付那畜生的经验也多,我们可还仰望着您呢!”
“哈哈!好小子,不愧是读过书的人,说的话就是中听。不过我也有些自知之明的,这大虫啊,不来便罢,来了就落不了我们的好。你可瞧好吧,万一……,我是说万一啊,万一那畜生真来了,你可别上头往前冲。找地方躲好。”
风信子一愣,看着猎户,竟无言以对。
猎户却不以为意,说道:“是不是很惊讶?庄子里谁还不是个混账东西?你别看这些人气势怪足的,我告诉你,没用!没有长弓劲弩,就凭咱们这些棍棒,毛用没有。反过来,这些人被那大虫一冲,瞬间就得溃散。到时候能有几个站稳的就算不错了。”
“所以说啊,你也别觉得自己就该舍生忘死,这词是这么说的吧?咱们都是贱命一条,能活下来再往长远了瞧。”
见风信子不言不语,猎户有些急了,声音提高了几度叫道:“咱今儿个跟你说的可是掏心窝子话,什么清高、什么气节、什么追求,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风信子摇摇头,试图把混乱的思绪甩出去,连忙安抚猎户道:“猎户大哥,您也别急。咱们可不一定就能遇见那大虫不是?”
“说得也是啊,你瞧我说的什么混账话,喝完热汤再说。”
“好!”
风信子跟着猎户进到后院,吴阿伯正在招呼夜里巡逻的人喝汤吃饭,见这两人一同进来了,微微眯了眯眼睛,嘴唇微动,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。
他叹了一口气,喊道:“庄里的老少爷们,算算时间,明日差役们也该从山里出来了,届时我找人去打听打听。大家再辛苦一晚,夜里关好门窗,起夜的也别出门,就在屋子里解决。一切明日再说。”
“阿伯您就放心吧,大伙儿都晓得!”
底下一片应声。
又过了盏茶时间,天色暗淡了不少。
老人、小孩、婆娘都收拾东西回家了,整个庄子都静了下来。
十几个汉子手拿棍棒,点燃火把,挨家挨户检查有没有关好门。
这一对人里,只有猎人背着短工、腰间别着匕首,全副武装着。其余众人加起来也不过有两三把柴刀,一个铁耙子还算得上武器。
风信子从家里带了短刀出来,却是借给了守院子的人了,他自己拎着铜锣,举着火把,跟着众人一遍一遍的巡逻。
夜里寒气刺骨,却没一个抱怨的。
因为庄子里的是他们的父、他们的妻、他们的子。
这守着的其实也是他们的一切了。
很快六个时辰过去了,至暗的时候也过去了。
巡逻的众人也说不上是失望还是高兴,总是无事发生,也都松了口气。
风信子从来没熬过通宵,只觉得腿疼、脑袋疼,浑身没一处不疼的。回到家,饭都没吃一口,沾床就睡。
苏爸也没叫他吃饭,一觉醒来已是下午。
“醒了?厨房里给你留了饭菜,我给你热去。”苏爸在院子里晒太阳,见风信子出来,说道,“午饭时候差役们回来了,这山里果真有虎。不过被他们给生擒了,不用担心。”
风信子大惊:“生擒了?”
“是啊,生擒活捉。据说准备送往宫里给贵人们赏玩。这畜生它就该在山里,有害除了就是,关到笼子里算什么?”
“您老什么时候也这么多愁善感了?只要不在咱们这儿,它爱怎么怎么。”
苏爸也笑了:“也是。哦,对了,吴阿伯找你。你吃完饭过去看看。”
风信子到吴阿伯院子的时候,这老伯正半躺在椅子上,一手摇着蒲扇,一手端着茶壶,美得不行。
“来了?来,坐。昨个猎户跟你说了不少话吧。”
吴阿伯没等他回答就接着说道:“你可别信那混蛋的话,他呀,可是个狠角儿。”
“早些年的时候,大概就是你还穿开裆裤的那几年,咱们周边这几座山上可是有狼的。大概有二十来个吧。”
“那时候猎户也跟你差不多,半大的毛头小子。他跟着他爹在山上打猎,他爹也是半路出家的和尚,哪会什么打猎啊。不过还好,不说多大收获,总算还是能混个温饱。过了大概两三个月,俩人越来越熟练,心也越来越野。”
“结果这一野,就出事儿了。那天俩人照常进山了,可到天黑了都没回来。一开始大家伙都没在意,毕竟打猎嘛,起早贪黑的,不奇怪。”
“可一直到了后半夜都没回来,他娘就坐不住了,连夜把我叫起来。我那时候吧,胆子也肥,找了几个不怕死的就上山找人去了。一直到天明都没找着什么人影,好在天亮了,大家伙一起进山找人。”
“我是在他家见到那小子的。当时都没个人样了。浑身是血,一裤子屎尿,见人来了也不说话,直打哆嗦。找着他的人说是在树上发现的,当时一大群人在树下转了好几圈,猎户愣是一声没吭。这小子是吓破胆了。猎户他爹没影,大家也没问,都知道多半人是没了。”
“猎户他爹到现在都没个衣冠冢。哎!可怜呐!”
吴阿伯长叹一口气,坐起来接着说道:“猎户回来以后痴痴呆呆过了大半年,知道吃饭也知道上厕所,甚至每天照常还能进山打猎,可就是不说话。把他娘给急的啊、各种方法都试了个遍,没用。”
“大家伙都以为他就这样了,其实也不错,不说话就不说话呗,能照顾好自己就行。突然有一天,猎户带着一身血回来了,一边叫一边哭一边跑。哭得那叫一个痛啊,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要抹眼泪。”
“还不等大家去问,第二天猎户就带着钱去城里换了铁锹跟短弓进山了,短弓就是他现在身上背的那个。这一去就是半个多月,没人知道这半个月发生了什么,不过从他再回来以后,周边几座山上就再也没听到过狼嚎的声音。”
吴老伯其实不是很会讲故事,但风信子还是听了一身冷汗出来。
微风拂过,只觉一身鸡皮疙瘩都出来了,三魂七魄都要被这风给吹走似的。
吴老伯撇了他一眼:“你是个有想法的,想做什么就去做嘛,你爹都不在乎了,你还怕什么。瞧瞧人家猎户,当年跟你也差不多年纪。你怕球?错了有能怎样?还能比他更凶险不成?”
风信子,啊不,苏家小子霎地蹦起来,长揖到地:“吴阿伯,我明白了!”
“你明白个锤子,滚蛋!”
(完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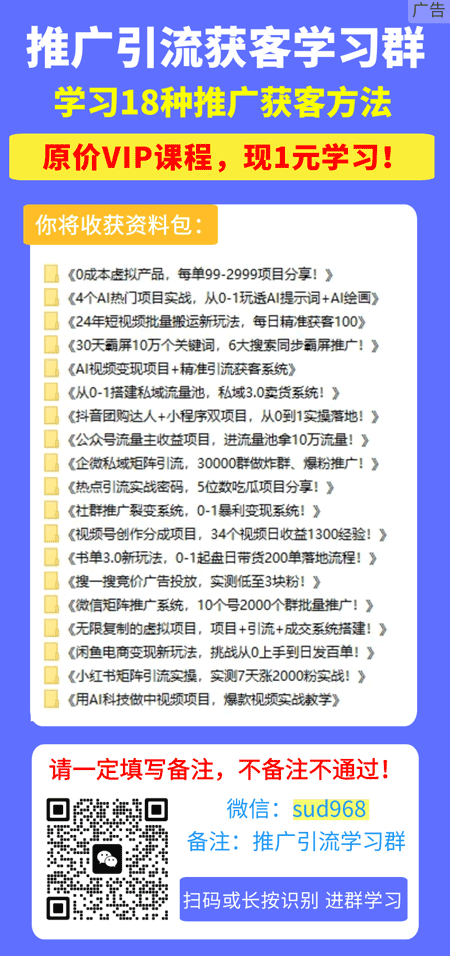
原创文章,作者:admin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seohomer.com/6314.html

